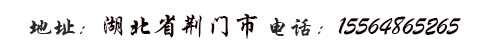藿香正气散及加减方学与用的思考
|
导读 借前人的学术经验和大家学习与重视“湿”---虽不是原创,但也是花了心思的小结,与大家共享之。 分享地点:基层中医之家 分享时间:-05-26 分享医生:湖南省临湘市向阳路向阳社区卫生室 王应红 借前人学术与经验和大家学习与重视“湿”---虽不是原创,但也是花了心思的小结,与大家共享之,如有不当或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指点,批评指正,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湖南多湿,湿病缠绵,我们一起探讨之。 一、五个加减正气散的学与用: 《温病条辨》的五个“加减正气散”,是笔者临床最常用之方,原因是,我是一个湿邪、湿病推崇者。(摘自王辉武的《老医真言》) 提起五个“加减正气散”,一定会联想到《局方》的“藿香正气散”的主治:“伤寒头痛,憎寒壮热,上喘咳嗽,五劳七伤,八般风痰,五般膈气,心腹冷痛,反胃呕恶,气泻霍乱,脏腑虚鸣,山岚障疟,遍身虚肿,妇人产前产后,血气刺痛,小儿疳伤。”原书推出的适应症的确很广,内妇儿,上中下都可治。是否准确?我们不敢苛求前人,但藿香正气散生命力之强,适应人群与病症之多,也是其他任何药物不能相比的。如今的藿香正气液、正气颗粒、正气水、正气胶囊、正气丸的畅销,就是明证。 当然,说藿香正气散好,并不是说能包治百病。吴鞠通针对当时一些看法,提出了异议,说:“按今人以藿香正气散统治四时感冒,试问四时止一气行令乎?抑各司一气,且有兼气乎?”他是从临床上发现其局限性,故在前人的基础上,参考当时的叶天士、薛生白等留下的医案记录,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创制了五个加减正气散,吴鞠通的这种学习方法和创新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他学《伤寒论》之三承气汤创制了五个承气汤,有人说他抄袭古人的经验,笔者认为,非也!学习中医要尊重传统,更应师古而不泥,学术要服务社会,适应现代,发展是必然的。吴鞠通的这种治学方法,我们都该认真学习。 五个正气散的总病机是“湿温之邪,蕴结中焦,脾胃气机升降失常”,并据其湿重程度、在脾、在肠和在经的不同,加减运用而有所区分。 五个加减正气散,都用藿香、厚朴、广陈皮、茯苓皮。 一加减正气散加神曲、麦芽、茵陈、大腹皮、杏仁;主治湿邪为主,升降失司所致的胃脘腹胀,大便不爽。对于大便情况,患者主诉为大便稀不成形,解不痛快,解了还想解;有的还说,大便粘滞,粘在便池中,水冲不净,此时遣用一加减正气散特别有效。 二加减正气散加木防己、大豆*卷、通草、薏苡仁;治疗湿阻经络的身痛,舌白腻,脉濡而模糊不清者。 三加减正气散加杏仁、滑石;治舌苔*而伏热较重者,其中杏仁利肺气,性辛淡而微温;滑石利水,为邪找出路。 四加减正气散加草果、楂肉、神曲,用于舌苔白滑,脉缓,湿伤脾阳者。 五加减正气散加大腹皮、苍术、谷芽,苦辛温,燥湿健脾,治腹泻脘闷,其大便稀水样,大便次数更多者,为湿浊较重、脾胃俱伤者而设。病重者可加车前仁以利小便而实大便;加干姜增强温阳祛湿之力。 五个加减正气散在应用上应抓住一个“湿”字,病位在中焦。以化湿、行气、健脾为总治则,并据临证变化,分别加上辛凉、辛温、甘温、苦燥、淡渗之品,以应对湿性粘滞、阴邪伤阳、易伤脾土、湿邪兼夹而难愈之特点。为了记住本方的临床应用与加减用药,笔者早年还自编歌括,以方便记忆,今录此以供参考。歌曰: 几加减藿朴广(皮)苓,一加曲麦茵腹杏,苡通防豆卷二成,杏仁滑石三加名,四用楂曲与草果,腹皮术谷五加定。 “一治溏便二经络,三治伏热舌苔*,四主苔滑脾阳弱,五治水便两俱伤。” 五正气散比较: 藿香:辛微温,入脾、胃、肺经。化暑和中、解暑发表。 陈皮:辛苦微温,入脾、肺经。理气健脾,燥湿化痰。 茯苓:甘平,入心、肺、脾、胃、肾经。利水渗湿,健脾和中,宁心安神 厚朴:苦辛温,入脾、胃、肺、大肠经。燥湿散满,行气降逆。 五个加减正气散均为“湿温之邪,蕴结中焦,脾胃气机升降失常”,所以治以祛湿除满,芳化渗泄,虽均用正气散为主方,但由于湿温病中的湿重、热重、在脾、在胃、在肠、在经的不同,方剂加减亦随病机有所差别。而五个加减正气散治疗各有所侧重,即一加减调升降,二加减宣经络,三加减利湿热,四加减运脾阳,五加减和脾胃之不同。所以吴鞠通在五个加减正气散方后云:“按今人以藿香正气散,统治四时感冒,试问四时止一气行令乎?抑各司一气,且有兼气乎?况受病之身躯脏腑又各有不等乎?历观五法均用正气散,而加法各有不同。亦可知用药非丝丝入扣,不能中病,彼泛论四时不正之气,与统治一切诸病之方,皆未见轩岐之堂室也,乌可云医乎!”吴氏此为精辟论述了用成方治病,要根据时令不同,脏腑差别,病机的变化,条分缕析,加减变化,方能切中肯綮,并纠正一方统治四时之病的偏颇。五个加减正气散虽为湿温病而设,但对临床选用成方作出了规范,临床中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附《温病条辨》原文) 篇名:中焦篇~湿温(附疟痢疸痹) 1.《温病条辨》条文:三焦湿郁,升降失司,脘连腹脤,大便不爽,一加减正气散主之。 注:再按:此条与上第三条,同为三焦受邪: (1)彼以分消开窍为急务。(2)此以升降中焦为定法,各因见证之不同也。 方剂:藿香梗二钱厚朴二钱杏仁二钱茯苓皮二钱广皮一钱神曲一钱五分麦芽一钱五分绵茵陈二钱大腹皮一钱水五杯,煮二杯,再服。 方论:(1)正气散本苦辛温兼甘法,今加减之,乃苦辛微寒法也。(2)A.去原方之紫苏、白芷,无须发表也。B.去甘桔,此证以中焦为扼要,不必提上焦也。C.祇以藿香化浊。D.厚朴、广皮、茯苓、大腹,泻湿满。E.加杏仁利肺与大肠之气。F.神曲、麦芽,升降脾胃之气。G.茵陈,宣湿郁而动生发之气。H.藿香但用梗,取其走中不走外也。I.茯苓但用皮,以诸皮皆凉泻湿热独胜也。 2.《温病条辨》条文:湿郁三焦,脘闷便溏,身痛舌白,脉象模糊,二加减正气散主之。 注:(1)上条中焦病重,故以升降中焦为要。 (2)此条脘闷便溏,中焦证也。身痛舌白,脉象模糊,则经络证矣。A.故加防已急走经络中湿郁。B.以便溏不比大便不爽,故加通草、薏仁利小便,所以实大便也。C.大豆*卷,从湿热蒸变而成,能化蕴酿之湿热而蒸变脾胃之气。 按: 方剂:(苦辛淡法)藿香梗三钱广皮二钱厚朴二钱茯苓皮三钱木防己三钱大豆*卷二钱川通草一钱五分薏苡仁三钱水八杯,煮三杯,三次服。 3.《温病条辨》条文:秽湿着里,舌*脘闷,气机不宣,久则酿热,三加减正气散主之。 注:(1)A.前两法一以升降为主,一以急宣经隧为主。B.此则以舌*之故,预知其内已伏热,久必化热,而身亦热矣。 (2)A.故加杏仁利肺气,气化则湿热俱化。B.滑石,辛淡而凉,清湿中之热。C.合藿香所以宣气机之不宣也。 方剂:(苦辛寒法)藿香三钱连梗叶茯苓皮三钱厚朴二钱广皮一钱五分杏仁三钱滑石五钱水五杯,煮二杯,再服。 4.《温病条辨》条文:秽湿着里,邪阻气分,舌白滑,脉右缓,四加减正气散主之。 注:(1)以右脉见缓之故,知气分之湿阻。(2)故加草果、查肉、神曲,急运坤阳,使足太阴之地气,不上蒸手太阴之天气也。 方剂:(苦辛温法)藿香梗三钱厚朴二钱茯苓三钱广皮一钱五分草果一钱查肉五钱炒神曲二钱水五杯,煮二杯,渣再煮一杯,三次服。 5.《温病条辨》条文:秽湿着里,脘闷便泄,五加减正气散主之。 注:(1)秽湿而致脘闷,故用正气散之香开。(2)便泄而知脾胃俱伤。故加:A.大腹,运脾气。B.谷芽,升胃气也。(3)以上二条,应入前寒湿类中。以同为加减正气散法,欲观者知化裁古方之妙,故列于此。(苦辛温法)(1)按:今人以藿香正气散统治四时感冒,试问四时只一气行令乎﹖抑各司一气,且有兼气乎﹖况受气之身躯脏腑,又各有不等乎﹖(2)历观前五法,均用正气散,而加法各有不同,亦可知用药非丝丝入扣,不能中病。(3)彼泛论四时不正之气,与统治一切诸病之方,指未望见轩岐之堂室者也,乌可云医乎! 方剂:(苦辛温法)藿柏梗二钱广皮一钱五分茯苓块三钱厚朴二钱大腹皮一钱五分谷芽二钱苍朮一钱水五杯,煮二杯,日再服。 二、藿香正气散一个临床运用十分广泛的方子,我个人也很喜欢使用(藿香正气胶囊,藿香正气颗粒用得最多),具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之功效。主治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证:恶寒发热,头痛,胸膈满闷,脘腹疼痛,恶心呕吐,肠鸣泄泻,舌苔白腻,以及山岚瘴疟等。临床常用于治疗急性胃肠炎或四时感冒属湿滞脾胃、外感风寒者。 下面就其临床运用谈一谈个人的一点心得体会:恶寒发热表邪重+荆芥、防风、羌活;腹泻甚+泽泻、车前子;热像明显时+银花、连翘、*芩(复方金银花颗粒);年老体弱者+*参;呕泻明显时合小柴胡颗粒;胃脘痛+高良姜、香附、肉桂(临床我常合用元胡止痛胶囊);秋季性腹泻+神曲、麦芽、石榴皮; 临床应用以恶寒发热,头昏重痛,上吐下泻,舌苔白腻、脉濡为辨证要点。 重点:本方选药兼顾表里上下,有芳化、燥湿、淡渗之功,根据表里寒热加减化裁,可用于三焦津凝气阻引起的各种证候。 三、湿病活血能增效 湿邪为病,临证最多。我国南方,地处卑湿,病湿者更为常见。中医传统公认:湿病多迁延难愈,难获速效。治疗湿病能否在原来疗效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呢?这是一个颇有探索价值的问题。 湿邪为病,临证最多。我国南方,地处卑湿,病湿者更为常见。中医传统公认:湿病多迁延难愈,难获速效。治疗湿病能否在原来疗效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呢?这是一个颇有探索价值的问题。 据笔者多年临床观察认为:湿邪虽属留着缠绵之邪,但湿病并非难治之疾,如能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巧妙地配伍活血化瘀药,往往能起到“催化”湿浊、倍增疗效的作用。今将拙见略陈于此,仅供同道参考。 湿病缠绵,多发难疗的原因在于湿邪为病甚广,无论外感或内伤,许多疾病都与“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怪叶天士当年也曾感慨地说:“吾吴湿邪害人最多”。究其原因,可能与气候、环境、饮食,以及人们的体质状况有关。如南方气候炎热,长夏较长,气温较高,雨水多,湿度大,长期处于这种难以用人力改变的环境中,为湿病的滋生提供了条件。正如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说:“天之热气下,地之湿气上,人在气交之中,受其炎蒸,无隙可避”。另外,南热之地,饮冷为常,饮食甘脂腥润者多,易使脾运受伤,水湿不化,又为湿邪内伏之原因。如此,内外合邪,故湿病较之其它疾病多见。 病既成,何以缠绵难疗呢?一般认为,湿邪的本性粘滞,从而决定了湿病的病程较长或反复发作。加上湿病多夹杂,症状纷繁,如误用滋阴则助湿,过用燥湿又伤阴,难以权衡,给治疗带来一些困难。除此之外,还责之于脾虚。多年来在理论上深入研究不够,停留于对‘湿”的笼统而肤浅的认识,未能揭示其规律所在,因此,提不出新的更加恰当的治法。这些都是导致临床疗效难以提高的原因。 湿病相关,尤在径在《金匮要略心典·痉湿暍病》中说:“中湿者,亦必先有内湿,而后感外湿,故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湿动于中,由是气化不速而湿浸于外,外内合邪”。说明湿之中人,无论内外,均主要取决于人体的气化功能正常与否,其中尤以肺脾肾三脏影响 。因此,传统的湿病治法,关键在于调畅以中焦脾胃为主的三焦气机,故有“善治湿者,不治湿但治气”的说法,这种“气化则湿化”的指导思想,经实践检验,有一定疗效,但并不理想。须知,生命赖气血之治,脏腑机能紊乱,首先导致气血失常变生诸病,正如《素问·调经论》所说:“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所以,治疗湿病只着眼于气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到“湿”及其与湿有关的饮、水、痰,它们同血之间的微妙关系。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寒湿》中说:“湿之为物也,在天之阳时为雨露,阴时为霜雪,在山为泉,在川为水,包含于土中者为湿”。深入浅出地说明了湿与水之间的关系,他还肯定地说:“湿之质即水也”。宋代严用和《济生方》认为:“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调摄失宜,气道闭塞,水饮停聚而结成痰”。明代张景岳还说:“痰之与饮虽曰同类……然饮清澈而痰稠浊”。前人的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湿、水、饮、痰异名同类的道理,以及它们在病理方面的源流关系。至于水湿与血的关系,唐容川的论述较为深刻,如他在《血证论·遗精》中说:病水者,亦未尝不病血也”。肯定了湿病与血分有关。日本长尾养治通过研究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认为“瘀血的形成不单是血循环的障碍,同时也有水代谢障碍,因此,讨论瘀血时,决不能忽视水的动态,血与水之间具有微妙关系”。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湿病致瘀的可能性。这就是:当人体三焦气机升降失调,水液运行受阻时,湿浊即可生成。 湿为阴邪,其性粘腻停着,容易影响血液流行,血行不畅,或湿滞伤络,可滞而为瘀,或因脾虚湿阻,脾运障碍,气虚不能摄血,离经之血为瘀,均可导致临床上常见的因湿致瘀的现象。而且,瘀血又反过来影响水湿的代谢,因瘀致湿,二者之间互为因果。过去有人提出“痰瘀同源”论、“*疸瘀血”论、“怪病多痰”论、“久病多瘀”论,也正是因为水湿与瘀血的恶性循环,构成了湿病难以速愈的病理基础。 于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治湿病,必须双管齐下,既化气利湿,又活血祛瘀,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疗效。 因湿致瘀须活血治湿病要活血化瘀这个问题,虽然未见有人明确提出过,其实,配用活血药以助利水除湿之治法,早在汉代张仲景就曾用过,如真武汤之配芍药,乃是通过“除血痹”以助化气行水湿;蒲灰散中的蒲*,消瘀利水,亦为活血除湿而设。这些方剂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有肯定疗效。笔者所提出的活血利湿法,是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于化湿方中配伍适当的活血化瘀药,如刘寄奴、泽兰、丹参、赤芍、红花等,其中刘寄奴和泽兰,具有化湿、活血的双重作用,既可以直接改善水湿运行和代谢,又可随着瘀血的消除,截断湿瘀之间的恶性循环,从而逆转病机,促进湿病痊愈。 湿病活血能增效活血化瘀法作为湿病的兼治通用法,随着近年的深入研究,已广泛用于临床,并取得了可喜的疗效。如肺心病,痰湿为患,水气凌心,舌质紫暗者;类风湿性关节炎,风寒湿痹久治不愈者;病*性肝炎,湿热缠绵难愈者;高血压、中风属痰湿上犯者;精神病、癫痫,湿痰蒙蔽清窍者。这些湿病或夹湿的疾病,有的有瘀证可查,有的暂无瘀证可见,配伍化瘀药后,疗效都有一定提高。说明湿病活血确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增效妙法。 刘寄奴:苦、辛,温。入心、肝、脾经。破血通经,消肿止痛,消食除胀。 泽兰:苦、辛,微温。归肝、脾经。活血化瘀,行水消肿。 活血化瘀兼渗利水湿者,如性寒凉之益母草、马鞭草、虎杖、半枝莲、穿山龙、木通、落得打等,性偏于温之泽兰、刘寄奴、天仙藤等,性平 不留行等。 现将几种湿病验案介绍如下: 1、湿温(上感) 此证初起头痛恶寒,身重疼痛,午后低热,酷似外感,但难以治愈,并以舌苔白厚腻、口渴不思饮为特征。可以在三仁汤中加泽兰、红花。 例1:王某某,男,50岁,年6月25日初诊。患者一月来,头昏闷痛,午后发热,上腹胀闷,纳呆倦怠,小便*赤,大便略稀,脉弦,苔白腻微*。查前医用药,不外三仁汤、霍香正气散之属,历时一个月未见显效,并谓湿热胶结,如油入面,病本缠绵,难求速效,嘱患者不必着急。此湿邪滞血之故,单化气不足以使湿化热孤。于是,乃以三仁汤原方加泽兰10g,红花3g,3剂,诸症悉减,腻苔渐退。唯腹胀,大便溏而不爽,胃纳未复,再进一加减正气散加红花3g,3剂收功。 2、湿痰(肺心病) 此证经年不愈,遇寒即发,痰多心悸,喘累浮肿,脉多弦滑,舌紫暗、苔厚腻多津,治疗颇为棘手。可以在真武汤中加丹参、葶苈子。 例2:郭森荣,男,68岁年9月25日初诊。患者咳嗽、心累、喘气反复5年余。平时咳嗽以早晚为重,痰多泡沫。近因感冒,咳嗽气喘加重,痰稠而*,夜间不能平卧,经用青、链霉素等西药治疗一周,痰有减少,但其它症状不减。查脉滑数,苔白厚多津,舌质紫暗,拟温阳除湿,活血化痰法,药用制附片、茯苓、赤芍、丹参、生姜、半夏、泽兰、葶苈子,水煎服,4剂痰减喘平,心悸、浮肿明显好转。 3、湿泻(慢性肠炎) 此证多久病反复,症见腹痛腹泻,大便稀薄而有粘液,便后坠胀不爽,可用乌梅丸(《伤寒论》)、半苓汤(《温病条辨》)加赤芍、红花、泽兰。 例3:冯某某,男,65岁,年4月5日初诊。患慢性腹泻约5年,大便稀,每日5一10次不等,并夹有白色粘液,曾住院数次,药用中西,反复难痊。见面色萎*,神疲纳少,舌苔*厚,舌质红,脉弦细。此脾虚生湿,湿郁生热,久滞瘀阻所致。乃以半苓汤加赤芍、泽兰,6剂大便逐渐成形,继以补中益气汤、鸟梅丸方加赤芍、泽兰巩固。随访一年未发。 4.湿痹(风湿性关节炎) 此证关节及身体疼痛,久治不愈,痛处不移,重着麻木,或有肿痛不红,屈伸不利,脉沉细,苔白腻而滑。可用薏苡仁汤加红花、刘寄奴、赤芍、全蝎等。 例4:蒋某某,男,60岁,年3月14日初诊。症见双下肢重着疼痛,麻木,发冷,痛处不移,关节略有肿大,经治疗3月,疗效不显。患者面色恍白,精神不振,苔白腻稍厚,脉细濡。此脾虚不运,内湿阻络之故。乃用六君子汤加砂仁、苡仁、淫羊藿、刘寄奴、赤芍、全蝎、神曲。水煎服6剂,诸症略有松解,再进6剂,则胃纳好转,疼痛消失,随访3月未发。 小结和体会 本文以临床和中医理论为依据,初步提出湿瘀相关理论和湿病宜活血的治疗方法。中医学的“湿”是独具特色的,临床上的“湿病”“湿证”大多数是现代医学在诊断和治疗上感到棘手的疾病。中医如何加深对“湿”的了解,提高对湿病的治疗效果,诚为当务之急。大量临床事实证明,“湿病活血能增效”,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问题,有必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验证和研究,以逐步为湿病增加一个新的、确有效验的治法。 湿病是湿邪蕴积于人体而产生的一类疾病。湿之为病,有外感六淫湿邪,有内伤脾虚生湿。湿为阴邪,其性重浊、粘滞,易闭阻气机,损伤阳气,多呈弥散状态而布散全身,甚为广泛。 湿邪对脏腑的影响以脾脏最为明显,脾喜燥恶湿,无湿困脾,则健旺通达,气血生化有源,运化转输功能正常。湿虽为土气,然湿盛则不流通,最易滞脾壅土,阻碍阳气,水津失布,而致湿病。脾亦主统血,脾气健旺,其统摄血液在血脉中正常运行而不溢于脉外,脾虚生湿或外湿入里后脾运不畅,必然影响血液运行不畅。 湿邪易兼挟它邪,如风、寒、暑、热、痰等,而致风湿、寒湿、暑湿、湿热、痰湿,既可阻滞气机,影响脏腑功能,又可流注经络脏腑,阻碍气血运行。 湿邪致病易引起血运失常,因此在辨证施治中合理加用活血药物会起到较好的配合治疗作用。如桃仁、泽兰、丹参、赤芍、红花等,既有利于湿邪的祛除,改善水湿运行和代谢,又能去除已成之瘀血,截断湿瘀之间的恶性循环,从而逆转病机,促进湿病痊愈。 体会:临床上疑难怪病多属“痰、湿、瘀、郁”为患,痰、湿、瘀三者互为因果,相互夹杂,只是各有侧重而已。故治疗时我们应该在治痰、治湿时勿忘加1-2味活血理气药,尤其是具有化湿、活血双重作用的刘寄奴和泽兰,理气化湿的陈皮等;活血化瘀时不忘加1-2味祛湿化痰之品,疏肝理气时稍加1-2味祛湿活血之品。这样互补互助,可起到增效防变的目的,为治好疑难怪病多出一条思路来。上期回顾:基层验案—婴儿咳嗽 《基层中医之家医集》——点击查看 所载内容皆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写留言”跟贴讨论。 基层中医之家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dancanf.com/dszp/3733.html
- 上一篇文章: 一池云锦新品婵皙水乳怎么样为什么这么
- 下一篇文章: 注意这11批次酒类和调味品不合格检